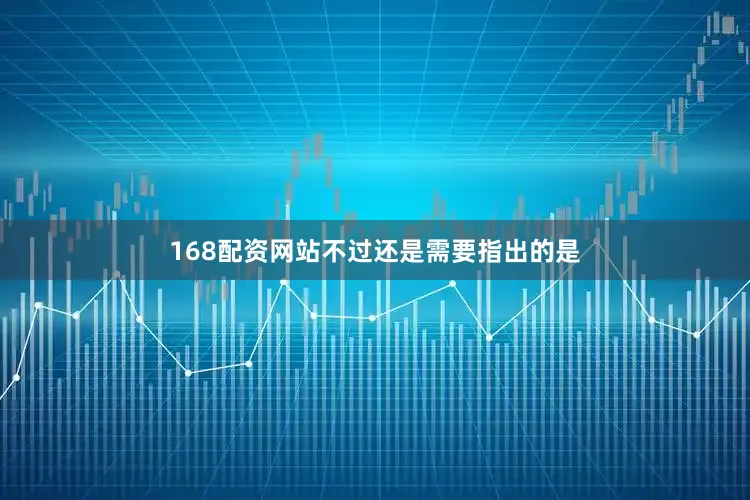毛主席两次挽留,胡适却铁了心要走,他到底在怕什么?
1948年的北平,风声鹤唳。城外炮声隐隐,城里人心惶惶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一架专机顶着寒风,在南苑机场焦急地等待着一位大人物——胡适。这可不是普通的撤离,这趟飞机的背后,是蒋介石的亲自安排,而另一头,是毛泽东捎来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“只要胡适不走,可以继续做他的北大校长。”
好家伙,一边是旧主的飞机,一边是新主的橄欖枝。换了别人,恐怕得辗转反侧好几个晚上。可胡适先生呢?几乎没怎么犹豫,拎起箱子,头也不回地就登上了那架飞往南京的飞机。他这一走,就再也没能回到这片他曾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土地。

很多人想不通,胡适到底在怕什么?是怕丢了官,还是怕没了钱?说白了,都不是。他怕的,是丢了他看得比命还重的东西。
这事儿得从头说起。想当年,毛泽东还是个湖南来的热血青年,在北大图书馆当个助理员,一个月拿八块大洋。这八块大洋是什么概念?也就够勉强糊口。而那时候的胡适,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教授,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,浑身散发着新思想的光芒,一个月薪水好几百块大洋。

当时的毛泽东,对胡适是打心眼儿里佩服的。他不仅旁听胡适的课,还把他发表在《新青年》上的文章翻来覆去地看,甚至一度在给朋友的信里,亲切地称呼他为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。那份敬重,是实打实的。可以说,胡适就是那个年代无数进步青年的思想启蒙者,毛泽东也不例外。
可两个人的路,从根儿上就不一样。胡适在美国喝了洋墨水,信奉的是杜威那套实用主义,讲究的是一点一滴的改良。在他看来,中国的问题就像一个病人,得慢慢调理。他写过一篇叫《五鬼闹中华》的文章,说中国真正的大敌是“贫穷、疾病、愚昧、贪污、扰乱”,而不是哪个具体的政权。所以他主张,大家应该先联手把这五个“鬼”给驱走了,国家自然就好了。

你琢磨琢琢磨,这套想法,放在一个和平年代,没毛病。可放在那个军阀混战、外敌入侵的乱世里,就显得有点书生气了。
真正的分歧,出现在1945年。抗战刚胜利,全国人民都盼着和平。远在美国当大使的胡适,心急火燎地给毛泽东发了封电报。电报里,他苦口婆心地劝毛泽东,让他“放弃兵权”,把军队交给国家,然后组织一个和平的政党,走议会斗争的路子。

这封电报,在胡适看来,是为国为民的肺腑之言。可传到延安的窑洞里,在毛泽东眼里,可能就有点天真得可笑了。毛泽东半辈子在枪林弹雨里闯过来,他最信奉的一句话是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。你让他放下枪杆子,不就等于让他自废武功吗?
所以,对于这封电报,毛泽东选择了沉默。一个字都没回。这个沉默,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有力。它像一道无形的裂痕,悄悄地横在了这两个曾经有过师生之谊的人中间。胡适不懂枪杆子的重要性,而毛泽东,也看清了胡适终究是个改良派的知识分子。

时间快进到1948年底,就到了咱们开头说的那一幕。解放军兵临城下,北平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。毛泽东心里还念着胡适的才华和声望,特意派人传话,许诺他可以继续当北大校长,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。这个条件,给得相当优厚,给足了面子。
可胡适为什么不接招?因为他心里那本账算得清清楚楚。1945年的那封电报,是思想上的分歧。到了1948年,他要考虑的就是更现实的问题了:他所珍视的“自由”还能不能保得住?他所坚持的学术独立,在新政权下还有没有空间?

他不是一个人在焦虑。当时和他一起登上那架飞机的,还有另一位学界泰斗傅斯年。傅斯年性格更刚烈,他曾放言,如果新政权来了,他只有跳海一条路。这种情绪,代表了当时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集体恐慌。他们怕的不是物质上的清算,而是精神上的禁锢。
胡适一辈子提倡“大胆地假设,小心地求证”,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思想被统一,学术为政治服务。他看着苏联的先例,心里直打鼓。所以,当那架飞机摆在面前时,他选择的不是一个政权,而是他所理解的“自由”。
这一走,便是永别。胡适先到南京,又辗转去了美国,最后落脚台湾,当了“中央研究院”的院长,继续做他的学问,直到1962年病逝。他在台湾的学术活动搞得有声有色,但他再也无法踏上大陆的土地,感受这片他曾深爱并为之奋斗过的热土的脉搏。
而毛泽东呢?在胡适走后,也彻底对他死了心。最初的那份敬重和挽留,最终变成了失望。后来,大陆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对胡适思想的批判,昔日的“偶像”成了“反面教材”。
回过头来看这段往事,真的很难用简单的“对”与“错”去评判。胡适的选择,是他个人信仰的必然结果,他忠于了自己的内心。而毛泽东的挽留与最终的放手,也是一个巨大历史转折中,一个革命领袖的现实考量。两个人,就像站在一个分岔路口,一个向左,一个向右,都坚定地走向了自己认定的方向。他们的分道扬镳,与其说是个人恩怨,不如说是一个大时代下,两种不同救国路径的必然碰撞。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,容不下太多的中间地带,这或许就是那个年代最大的无奈吧。
大象配资-十大可靠的配资公司-炒股配资皆-线上股票配资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股票金融配资科创债ETF博时最新规模达100.38亿元
- 下一篇:没有了